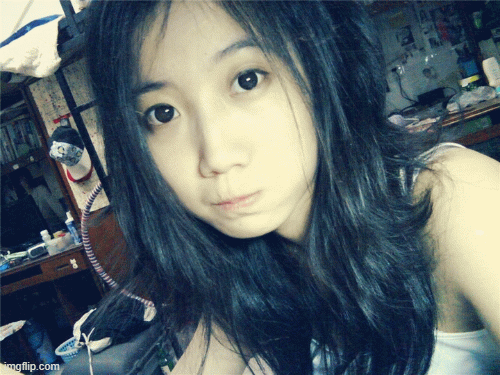学问批判|重拾两个“凡是”,绝对不是蠢而是恶一早醒来看到许多朋友都在转发或议论四十多年前《光明日报》刊登的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这篇文章现在读起来似乎很幼稚,因为文章洋洋洒洒六、七干字,绕来绕去,讲的实在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常识:对与不对,不应该由谁说了算,而是要让事实说话,换句话说,也就是要有证据。
也许让今天的人觉得好笑的是,这样一个简单常识的确立在1978年竟然需要异常的勇气。更让今人觉得费解的是:既然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这篇文章应该是以实践或事实为论辩的主线。但事实并非如此,为了确立这么简单的常识,这篇文章所主要依据的还是已故领导人的话。按照论辩的规矩,这位领导人的话是不能作为事实论据的。实践是否是检验真理的唯一的标准,这不能由某个领导人或其他领袖人物说了算。这个命题成立与否需要事实论证。
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大概很难理解当时作者的难处。那时的人除了有一种类似宗教似的忠诚以外,还真养成了一种类似宗教的思维范式:是非判断的依据就是在领袖的红宝书里寻找答案。
我小学一年级赶上了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刚开学老师就让我们背诵“为人民服务”。后来小红书人手一册,不管是语文课、算术课或其他什么课程,老师上课必引用小红书里的话。那个时候无论议论什么,我们都会自觉地从小红书里去摘录一段话,然后鹦鹉学舌发挥一番。记得当时记叙文引用最多的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一段到今天我还背得滚瓜乱熟的语录。
不过那时的作文,批判文章占多数,也就是老师会给我们一个错误观点,让我们去批判。现在想想还真是搞笑的:许多错误言论我们当时还真理解不了。可那时最大的烦恼不是理解,而是在红宝书里如何找到相关的语录!大多数文章的开头都是“伟大领袖XXX教导我们”。后来我们都模仿大人找到了一种应对的路子,那就是任何错误观点都是阶级敌人的观点,因此“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或“干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类语录就成了百贴灵。
当时的套路,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写作“范式”,是很简单的。在引用了伟大领袖有关阶级斗争的话之后,然后就是一两句诸如“东风吹,红旗飘,祖国形势一片好”的话,紧接着用一个“但是”引出阶级敌人亡我的不死之心。批判有两步,首先点明这话违反了领袖的观点,这似乎不用证明;第二步就是因为这话违反领袖的观点而判定说这话的人是阶级敌人,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牛鬼神蛇。判定之后就用“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坚决不答应”这样的套话义愤填膺地叫开去,同时抡起“反对搞复辟”的棒槌,一打一个“准”。
回想起来觉得真是蠢,蠢得连我自己都觉得费解和好笑。可细细地思想开去,却也不能用一个“蠢”字了结的,因为当时我们所能读到的东西就是官媒的报章,所看到的文字都是官准印刷的。不仅文字如此,收音机只能收到官方的声音,BBC或VOA都属于敌台。一般的家庭也没有可以接受信号的短波收音机,就是有也不敢听,因为那是通敌罪。说老实话,我那时也从来没想过要去听这些电台。那时唯一有一点点多样化信息的是经过多次过滤的《参考消息》。用现在的话来说,整个国家就一个信息大茧房。再聪明的人,如果他/她的所有信息源都很单一,认知环境只有这点资源,他们很难摆脱这种思维套路的。
用认知心理学的理论来分析当时的状况,也许我们可以这么说:打小背诵的领袖话语给了我们认知世界的知识框架和工具,由于这些话是我们唯一的认知工具,我们的认知变得高度套路化。当套路化思维成为习惯之后,我们的认知就成了不假思索的自动行为。认知的套路化虽然能让我们非常方便地认识问题,但也闭合了我们的认知视野。
对领袖的无限忠诚又大大加固了思维套路化的陷阱,使个体思维完全挣脱不出来。用阿伦特的话来说,个体的思想停摆了。由身份认同主导的思维,其害处远远甚于信息控制。身份认同思维范式既控制人的思维方式和过程,也控制人的情感和亚意识。身份认同主导的思维就是看齐思维,是忠与不忠的身份认同的情感表态。所谓的思维,实在是一个幻觉或假象,因为个体要做的就是按既定的标准节拍小心翼翼、满腔热情地去跳忠字思维舞。记得当时写文章最害怕的就是站错了队。
我这简单的回顾也许能让读这篇《光明日报》文章时产生的费解变得不那么费解。1978年虽然“四人帮”已经倒台了,但这种主宰了许多年的身份认同式思维范式已经成了大多数人的根深蒂固的思维习惯。《人民日报》有一篇叫“学好文件抓住纲”的文章非常典型地表现出了这种思维范式的顽强。这篇文章的结论是后来非常著名的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当时的学者意识到,要突破这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还得以其人之矛,攻其人之盾。唯有依靠身份认同的思维范式去论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么简单的观点才可能得到大家的情感响应。过来人都知道,这篇文章的观点是遭到许多人反对的,因为这篇文章掀翻了大多数人的认知框架。
我真不知有多少人会去重读这篇文章,更不知有多少人会珍惜这篇文章的贡献。在这篇文章发表的那个年代,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大家都跌入到单一的思维陷阱,显得非常愚蠢。今天大家之所以转发这篇文章,除了纪念这思想史上的里程碑之外,可能还有对再次跌入陷阱的担忧和恐惧。因为具有捉弄人意味的是,在网络这么发达的今天,信息茧房的构建竟然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如果再来点身份认同,那重蹈身份认同式的思维范式也不是没有可能的。然而要强调的是,在信息发达、思维方式多样化的今天,如果还有人想重拾两个“凡是”,那他们绝对不是蠢而是恶了。
我只是想问,在我们笑过我们自己的愚蠢之后,我们还会再被我们的子孙笑话吗?
2022/05/11
业余人间观察员|丧事喜办:从庚子事变到灾难兴邦,一场不切实际的幻想
丧事喜办,顾名思义,是指把丧事当成喜事来办,这在民间被称为“喜丧”。
中国自古就有这种风俗。在民国人徐珂创作的《清稗类钞》中,有这样的记载:
引用
“人家之有丧,哀事也,方追悼之不暇,何有于喜。而俗有所谓喜丧者,则以死者之福寿兼备为可喜也。”
也就是说,死者必须“福寿兼备”,其丧事才能称之为喜丧。“福备”即儿孙满堂,门丁兴旺;“寿备”即年过80,寿终正寝。
当然,称之为“喜丧”,只是表现出一种人们对于正常死亡的豁达。而丧事终究是丧事,亲人离去所带来的悲痛实实在在,不是一个称谓可以轻易抹去的。

《杨门女将》喜丧剧照
到了现代,“丧事喜办”一词就像近些年流行的“内卷”这个人类学名词的泛化一样,开始逐渐衍生出别的内涵,用来指代一些美化灾难与过失的行为。
这个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泛化的似乎已经无从考证了,我仔细检索了一下发现,目前能看到最早这么使用的例子,是天涯论坛里的一个帖子。
帖子的名称叫做“【新闻纪实】把丧事当喜事办!”
帖子的内容是:
2.21某新闻报道
(此处原本是图片,但已不可见)
报道文字:
引用
昨日,xx县人民政府在xxxx中学为xx同学颁发”革命烈士”等荣誉证书。
2003年9月29日,为抢救两名落水同学,xx同学奋不顾身,献出了年仅14岁的宝贵生命。
为此,市政府特批xx同学为”革命烈士”,xx县政府还授予xx同学”见义勇为先进分子”光荣称号。
图为烈士家人在同学们的掌声中接过荣誉证书。
此后,“丧事喜办”这个词逐渐流行开来,每逢此类事件发生,都会见到它的身影。
比较有名的如2009年“楼歪歪”事件、2010年大连油管爆炸事件、2011年动车事故、2013年青岛油管爆炸案等等,不胜枚举。
在这些公共安全事件中,不仅有广大网民参与,也经常能见到官媒与地方媒体亲自下场,只是他们扮演的角色有时候略微不同。
比如2013年的青岛油管爆炸案。在这起62人遇难的惨剧下,青岛本地媒体不仅没有刊登灾情,深入报道。反而连续发出《官兵做饭百姓喊香》《排队献血爱暖寒冬》《水电气已通,生活步入正轨》《住安置点如家温暖》等等新闻。

2013年《青城早报》
这一系列报道让人不禁疑惑,这哪里是灾难现场,简直是人间天堂嘛。难怪当时有网友讽刺说:换个标题吧,干脆叫"人民群众喜迎管道爆炸!″
再比如同年2月在造成10死12伤的河南义昌大桥垮塌事故中,新京报发表名为《一篇事故报道怎么那么多“领导重视”》的社论批评河南本地媒体大河网说:
引用
有网友指出,“1300字,提到16位省市领导的重视,1134字表扬河南省委省政府如何辛苦工作;其中褒扬用语25处,如
�迅速、立即、有序、精干、全力以赴、难度很大、全力救援……’没有出现一次伤亡人员或家属名字,没有家属一滴眼泪、没有一句对政府的批评,没有一声领导的道歉……”
一场突如其来的爆炸垮塌事故让10位同胞罹难,令多个家庭陷入悲痛。人命关天,报道却寥寥数语;死者为大,却大不过领导的“重视”。说这篇报道眼中只有官员,而没有民众,或许不为过。塌桥废墟之上,“人”不见了,只留下对当地政府、官员的大篇幅褒扬,这是对生命的漠视与麻木。
虽然大河网马上做出反应,写了一篇题为《千字新闻稿提多位领导的背后———谁该被吐槽?》的文章辩解称“报道只是大桥坍塌专题中的一篇,把这一篇文章割裂式地拿出来讨论,有断章取义、以偏概全的嫌疑”并说
“新闻的生命力来自于准确、真实和全面,说事实、只说事实、说全部的事实应是每个新闻人的自律。”不过次日,羊城晚报发了一篇名为《“丧事喜报”怪官员也要怪记者》的文章,毫不客气的驳斥了回去:
引用
这篇报道确实非常“全面”,从河南省委书记、省长、副省长、安监局长、公安厅、卫生厅,到三门峡市委书记、市长、市领导等一路“点名”,简直就是电影《一个都不能少》的现实诠释。它之所以引起反响,是因为它几乎“全面”地契合了中国事故报道的常见格式:事故发生后,引起__的高度重视,__当即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抢救伤员,查明事故原因,积极做好善后工作;__连夜赶往__现场,看望伤员,随后召开__会议,部署施救和善后工作,__在发言中强调要认真贯彻执行__的批示,并要求举一反三吸取__教训,立即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__成立了以__为首的事故应急处置小组,__。目前,事故相关责任人已被警方控制,现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中,广大群众情绪稳定……
据说美国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很爱面子,无论在什么场合,他都要当主角。“我父亲不喜欢参加婚礼和葬礼,”他的儿子回忆说,“因为在婚礼和葬礼上他既不能当新娘,又不能当死者。”
可是我们的一些人比罗斯福更“爱面子”———哪怕在惨烈的灾难事故中,也仍然像个救苦救难的绝对主角!
看到这儿,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恍惚。请不要怀疑,这些情景的确是当年媒体报道的真实写照,也是大众对于“丧事喜办”的普遍态度。

现如今,“丧事喜办”这个词的用武之地越来越多,但批评的音量却越来越小,曾几何时对此义愤填膺的各大媒体们也都悄然换了阵地——也许,有人真的需要这种内心的热量与精神的寄托吧。
追溯过往,其实不难发现,虽然“丧事喜办”的另一层内涵被应用的时间不久,但这种现象却自古有之。
举凡天灾人祸,必有歌功颂德。1900年,庚子国难,慈禧挟光绪出逃。当时率军勤王,在老佛爷轿前护驾的甘肃布政史岑春煊后来撰文回忆称:
引用
“太后御蓝布衫,以红棉带束发。帝御旧葛纱袍,当盛暑流汗,胸背粘腻,蝇蚋群集,手自挥斥。从行宫监,皆徒手奔走,踵穿履破,血流沾洒。”
这等狼狈景象可比当年唐玄宗溜去四川要惨得多了。难怪岑春暄感叹:
引用
“窃叹前史所述,人君出亡苦况,千载相同,不谓平日见于记载者,今乃身亲睹之。”
在朝廷都自顾不暇,社会秩序崩坏的情况下,老百姓将要承受何种灾难,可想而知。

八国联军进入紫禁城
然而尽管犯下如此巨大的错误,慈禧却没有丝毫反思悔过之意。在满足了列强的赔款索取、惩办“祸首”、签订《辛丑条约》等条件后,慈禧居然下旨大赏“功臣”,好像这不是一次耻辱,而是一场胜利。
所有人都沉浸在这场庆功宴之中,唯有满怀报国之志的军机大臣瞿鸿禨不揣冒昧,上了一道折子,其中说:
引用
“臣顷蒙恩典,实万分不安。现当时局艰难,诸事都宜核实。恩旨一出,中外瞩目。若有幸滥,何以示天下?”
意思是说:首先,我无法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份恩赏。其次,眼下时局艰难,内外动荡,若在这个时候大肆封赏,不仅容易出现诸多纰漏,且拿什么跟天下人解释呢?
不过此时的慈禧已然忘了逃亡途中的悲惨与凄凉了,哪里听得进劝谏。回到紫禁城,依旧“兴高采烈”“大事铺张”。
其实,在回来的路上,岑春煊一直在不停喟叹:“殷忧启圣,多难兴邦”。通过这种方式,他将自己与国家遭受的苦难通通合理化并将其幻想成一种通往胜利所不可或缺的东西。
然而,他却忘了:
若反思不彻底,则灾难无意义。果然,十二年后,他亲眼看着这个帝国在最后的一次灾难中轰然倒塌。
每日一语
赞(55)